神奈川立飲文化講座第5卷“邊界與交流”

2015.5.8 文:井上明子 圖:西野政正
藤原力
BricolaQ 編輯、評論家、總監。 1977年出生於高知市。 12歲時,他搬到東京,開始在東京獨自生活。此後,他經常搬家,在一家出版公司工作後,成為自由工作者。負責編輯武藏野美術大學公關雜誌《mauleaf》和世田谷公共劇場《Caromag》。與 Riki Tsujimoto 合編《建築書籍指南》(名月堂書店)。與德永恭子合著《最強的戲劇理論》(飛鳥新社)。目前居住在橫濱。 F劇場中心成員。此外,他還在各種地方創作了“Geki Quest”,你可以拿著遊戲書在城市和半島中漫步。
皮仁寧次
1980年出生於秋田縣。 2000年至2004年期間,他隸屬於Dairakudakan,師從Maro Akaji。她以舞踏所培養的獨特身體性為基礎,呈現了對自己身體進行微觀處理的獨舞,以及對身體進行物質性對待的編舞作品。近年來,他不斷觀察歌曲和舞蹈的創作體系,提取個體身體和生活中累積的元素,試圖將當代舞發明為現代都市的民間表演藝術。 2011年,她獲得了橫濱舞蹈收藏EX評審團獎和藝術節/東京公共參賽項目F/T獎。出現在約瑟夫·納吉、FAIFAI、ASA-CHANG & Jilgrimage、岡田敏樹等人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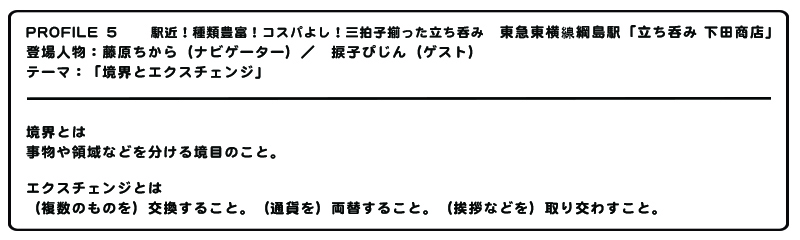
這次,我們將在距離綱島站步行 2 分鐘的立見下田商店與舞者兼編舞家 Pijin Oshiko 進行聊天。我們的領航員 Chikara Fujiwara 從馬尼拉製作回來後的第二天就抵達了。寧次子擔心兩人見面時藤原的臉色發紫,但她也表示,在完成從京都到韓國到福岡的考察旅行後,她胃部不舒服。兩個陷入低谷的人帶給大家的《站著喝酒文化講座》第5期的主題是「邊界與交流」。
Chikara Fujiwara(以下簡稱藤原) :嗯,看來日本已經進入了冷卻期。
Oshiko Pijin(以下簡稱Oshiko) :不過今天很熱。
藤原:今天的主題是寧次子跨越了舞蹈和戲劇的界限,也往返於韓國和日本之間,所以有一個「邊界」人的形象。此外,當您跨越國家和邊界時,您會嘗試透過交換某些東西(例如交換貨幣)來生存。我決定設立這個計畫是因為我想聽聽 Oshiko 先生對這種界線和交流的看法。
寧次子:首先,說到界限,Chikara-san從馬尼拉回來後感覺不舒服,但我的胃病也已經有一個星期了...儘管我在韓國和京都看到了很多東西,但我仍然難以消化資訊。在參觀了京都的當代藝術和韓國密陽阿里郎節後,我在去福岡的途中拜訪了我的朋友、舞者手塚夏子,但那天晚上我發了高燒,把我積攢的所有東西都扔進了浴室。這就是為什麼我在過去的一周裡一直處於一種內部器官之間沒有界限的情況下。今天想吃米糠泡菜,拿乳酸菌,一點點講講如何分割內臟。
藤原:原來如此(笑)
那麼,您想乾杯嗎?
俊子:是的。
乾杯!

藤原:不過,走來走去還是很累的,不是嗎?
Nesuko :特別是因為我是一個只能看到眼前事物的人,當我在另一個地方工作時,我無法想到東京。我目前在東京創作作品,但我沒能把在韓國所做的東西帶回東京並加以利用。
藤原:我也有同樣的情況。當我在馬尼拉時,我不太喜歡看日本新聞。
Nesuko :現在就讓我們盡情享受綱島。
藤原:是啊(笑)


下田商店入口處有一個托盤,把想吃的東西放在上面,然後拿到收銀台。
當你在後面的配菜角點餐時,工作人員會將你的食物加熱並交給你。
如果您的桌子上或冰箱裡沒有烤雞肉串或油炸食品,他們會為您烹飪並在您點餐後送給您。
Oshiko :我一直在談論我的病,但去年六月我在釜山進行製作專案時,由於壓力而患上了尿道炎。我覺得釜山人總是和某人在一起,彼此之間的界線很鬆散。即使當我想獨自思考時,也會有人走進房間,用蹩腳的日語說「你喜歡 AKB 的誰?」之類的話。那是相當痛苦的。那時,我開始意識到自己與他人之間的界限,我認為舞蹈可能是一種消除自我界限的人為技術。我再次意識到,我喜歡舞蹈,因為它是一種服務場所、參與運動、成為一種不做自己的過程。
藤原:啊,我想我明白了。有來自澳洲和美國的人來到馬尼拉,他們都很善於交際,所以如果我一個人在咖啡館工作,他們總是會和我說話。感覺很自然。至於菲律賓人,他們很喜歡說話,所以他們最後就跟我說話了(笑)。但當我生病時,我以為我不想再說英語了,就讓我一個人待著…
寧次:菲律賓口音的英語叫什麼? 菲律賓語 希臘語? ?
藤原:菲律賓有 7,100 多個島嶼,顯然有 172 種母語,但馬尼拉說的是他加祿語。他加祿語口音的英語稱為 Taglish。與澳洲口音相比,使用 Taglish 的人的英語更容易理解。英語是菲律賓的官方語言,但由於我不是該語言的母語,我聽說人們在談到英語時感到有點猶豫。似乎這種情況常常會變得痛苦,這被稱為英國恐慌。
現在,我們去喝第二杯吧?
俊子:那就好。我對 Gari Highball 很好奇...
藤原:那我就去烏龍高中。

「Gari Highball」是一種上面加有gari的高球威士忌。
俊子:誒!加里就是這個溝壑!我以為你是說脆脆的高球威士忌(笑)

關於口音-土方辰巳和寺山修二
藤原:繼續我之前說的,菲律賓人英語說得很好,部分原因是國家政策。換句話說,我總覺得我有兩種或多種語言。這太棒了,不是嗎?
Oshiko : Chikara-san,你是高知人,對吧?土佐方言和標準日語完全不同嗎?
藤原:啊,那完全不一樣。秋田話和標準日文有什麼差別?
Toshiko :顯然,我一接到通知就開始語調。 「Ka (ka-)」變成「ga (nga-)」。然而,雖然很容易理解口音和標準日語的區別,但表達起來實際上很奇怪,因為口音在前,標準語言在後(笑)
藤原:當然。順便說一句,關於像您一樣來自秋田的舞踏舞者土方辰巳的口音,您之前指出這是失去口音的人的語言。
寧次:是的。我認為土方先生是一位積極整合東北的人。他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有現代舞背景,他創造了一個全新的術語,叫做「舞踏」。這是一項了不起的發明,我認為他們確實經過深思熟慮並取得了突破。
說到方言,我聽說土方葬禮上的弔唁禮物是土方說話的錄音。有一家公司把它做成了CD,現在賣得相當高的價格,當我聽的時候,我想,“啊,這是他們製作的秋田話。”就我個人而言,我能夠從遠處觀察一直被神化的土方先生,這讓我意識到創造一些原創的東西而不是僅僅做“舞踏”就成了。
藤原:原來如此。順便問一下,同樣來自東北的寺山修二呢?
寧次子:我不認為寺山先生的口音是他創造的。雖然我是比當地人更容易聽話的類型,
我覺得這和土方的操作方式不一樣。我真的很喜歡他說話的方式,這是他的身體動作和津輕口音的混合體。
藤原:這可能和今天的主題「交流」有關,但是當你在某個地方時,你吸收了很多東西,當你和周圍的人交談時,你使用的詞語有很大的影響力我會接受,對嗎?有趣的是,個體身上仍保留著不同土地的痕跡。
戲劇作為媒介
Oshiko : Chikara-san,你這次去馬尼拉的原因是為了話劇《Quest》的駐場製作,對吧?
藤原:是的。 TPAM2015之後,那邊的導演邀請我參加一個年輕的節日,叫做KARANABAL2015。事實上,這個節日似乎是一個三年計畫。今年是第一年,所以我專注於研究,並透過將我在馬尼拉每天拍攝並保存的鏡頭和我在那裡採訪的故事拼湊起來創作了一個小作品。
Oshiko :嘿,順便問一下,《Geki Quest》的最初靈感是什麼?
藤原:這一切都是從井狗谷的藝術空間 blanClass 的請求開始的。我說:「為什麼不嘗試呢?」(笑)我小時候常常看遊戲書,所以我覺得在外面玩可能會很有趣。然而,馬尼拉有安全問題,所以我認為我不能做同樣的事情,所以我想如果我能看看這座城市,見見人們,聽聽他們的故事,並從那裡建造一些東西,那就太好了。這就是為什麼我不關心格式。
所以,我不知道這是否是我們的共同點,但你最近一直在談論「媒體」。其實我也認為Gekiquest是一種媒介。也許是因為我自己就是一名編輯,但我認為《Geki Quest》讓我可以和很多人交流,它可以讓我收集很多東西,打包它們,然後編輯它們。 Oshiko先生,您所說的「媒體」是什麼意思?
奈須子:如今,所謂的媒體已經不再是媒體了。或者更確切地說,需要識字。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戲劇現在可以扮演這個角色。我不認為世界上發生的事情不會對我的身體產生影響,但從這個意義上說,當我去劇院看戲劇時,我對這個世界有了更多的了解。
藤原:啊,作為當今世界的反映。
俊子:是的。即使你什麼都不考慮地過著自己的生活,你的身體裡一定有一些東西被寫下來,當然即使你在舞台上表現出來也不會傳達出來,但我認為會有一個製作來帶來它奧特群島。至少這是我想要關注的。
事實上,大約在2003年4月,當我拼命追隨當代舞界時,我的腦海裡有一種模糊的感覺,“我想知道現在世界正在發生什麼。”我去看的作品沒有涉及任何社會問題或帶有任何政治訊息,但透過觀看它們,我有一種了解世界正在發生的事情的感覺,它就在我作為觀眾的內心。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當時的現代舞動作起到了媒介的作用。當時我就有一種感覺,去ST點,我會學到一些東西。
藤原:太棒了。當你去ST景點時,你可以了解一些關於現代日本的知識,對嗎?
寧次:是的。確實是這樣的感覺。但現在我覺得扮演這個角色的是戲劇,而不是舞蹈。

藤原:最近,我聽了高秀吉的《猿類戲劇理論》講座,他談到了“戲劇在古希臘的作用”。例如,某媒體向雅典公民播放一部戲劇,內容是「我們現在正在遭受斯巴達的攻擊,我們該怎麼辦?」或展示亂倫的倫理,大家看完後議論紛紛。
Naeja :我認為這是一個類似的話題,但我實際上去韓國看了一個叫做密陽阿里郎節的節日。我聽說可以在那裡觀看密陽白州海苔傳統活動的表演,所以我沒有參加主要的節日而去了那裡。密陽阿里郎節的結尾是一場壯觀的多媒體表演,其中有從河裡吹來的霧氣,河後面的一座山,以及山頂上的一座寺廟,它被點亮並伴隨著激光燈光。伴隨著雷射燈光,還有一個小品,講述在殖民時期遭受日本軍隊壓迫的韓國人民被密陽治安組織拯救的故事。當然,日本軍隊也出現了,並且有一個很長的場景,他們射殺當地居民。
當我看到它時,起初我以為這是某種宣傳劇,但當我回到福岡並與我的朋友手塚夏子談論它時,我們開始談論「健康的民族主義和不健康的民族主義」。在這種情況下,韓國是健康的,日本是不健康的,這對我來說是有道理的。希臘戲劇也是如此,我們消化過去所陷入的可怕歷史的過程正在被改編成戲劇並被一遍又一遍地觀看。所以這根本不是宣傳。這也與戲劇本身是一種媒介有關,但我認為正確地觀看這樣的戲劇並不是抗日教育,但戲劇仍然是一個必要的過程。另一方面,日本有能力忽視事情或說“沒關係”,然後每年重新設定。簡而言之,就韓國和希臘而言,劇院是一種讓人們看到他們不想看到的東西的裝置。
藤原:從這個意義上說,chelfitsch的岡田先生最近創作的作品可能很清楚這一點。 “我們如何展示我們不想看到的東西?”
Neshiko :我想知道這個過程是否也應該在日本進行。但我覺得不會有人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覺得我是一個不關心日本的拉丁人。
藤原:我想知道它是從哪裡來的。我感覺戰後就有一種「不想看」的感覺…
Oshiko :日本人擅長在不需要任何人做出決定的情況下讓事情順利進行。
藤原:那可能是很古老的事了;例如,《被遺忘的日本人》(宮本常一所著)中出現的對馬老人的故事就是這樣。他們應該談論某個話題,但他們沒有進行討論,而是回憶起諸如「很久以前發生過這樣的事情…」之類的事情,在你意識到之前,你已經得出了結論。
Nesuko :日本人做了很多他們不適合的事情。辯論和民主。
藤原:事實上,隨著全球資本主義的出現,你可以說我們覺得我們必須在全國範圍內發展我們的經濟,我們必須善於辯論。然而,儘管我說過日本的優勢之一是不做決定,但我也覺得我們正被迫進入一個除非以一定速度做出決定否則事情就不會前進的社會。順便說一句,當我從馬尼拉回來時,一個美國人問我“我想你”用日語怎麼說,我想了想,回答說:“是嗎?” ? ?
俊子:嗯…
藤原:有一個著名的故事,夏目漱石將“我愛你”翻譯成“月亮很美麗,不是嗎?”如果「我想你」是一個古老的日語單詞,我想它會透過和歌詩來傳達。所以至少要5、7、5,如果可以的話,5、7、5、7、7就更好了(笑)。
寧次子:好長(笑)好長,而且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所以直接說「我想你」不是更好嗎?
藤原:是的(笑)如果我們是一個需要5、7、5、7、7來表達我們感情的種族,我們可能會在全球國際競爭力的世界中被拋在後面等等。然而,我不想那麼輕易地說出「我想你」。

與舞踏的邂逅
藤原:另一方面,我讀到了一篇關於您如何發現舞踏並加入大樂館至今的採訪,這就像一塊“滾石”(笑))
寧次:哈哈
我會連結到媒體的話題,但以能劇為例,有一種感覺,一種代代相傳的某種表演藝術是寫在能劇演員的身上,而不是「這個能劇演員的舞蹈」 」我想是的。同樣,這不是關於我的,而是關於“寫在我身體上的這種表演藝術”,這是一種身體作為媒介而存在的感覺。自己走路的三歲奶奶背著出來,跳了幾分鐘舞,然後回家了。那真是太好了。隨著年齡的增長,你的歷史、你從事的表演藝術、你度過的時光似乎都寫在你的身上,而不是作為舞者。這就是為什麼我是一名舞者,但這不是舞者所做的,所以我覺得這不是我。這種感覺對我來說真的很好。第一個想到的人就是大野一夫。大野的自我已經被覆蓋在他的身上。這就是為什麼我覺得是大野一夫幹的,而不是大野一夫。我確信有一種到達並了解這種領域的感覺,所以我想我想活那麼久。
藤原:原來如此。我想這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押子從一開始就突然跳入舞踏的核心。我想你可以說,在你2000年加入的時候,Dairakudakan已經變得相當歷史化了,也許有一種感覺,你可以透過Dairakudakan觸摸身體表達的歷史,不是嗎?
俊子:這可能是真的。當談論舞踏技術時,關鍵是如何創建一個以不像你的方式移動的系統。簡單來說,這只是一個釋義,例如“舉起你的右手”而不是“舉起你的右手”,“你的身體已放置”而不是“站立”,以及“抬著你的腳”而不是「走路」。我認為如何以這種方式讓自己處於「不是我」的狀態是一種技巧,也是舞踏的特色。所以我想這正在影響它。
藤原:你認為你首先為什麼適合那裡?
俊子:我想知道為什麼…
我去看了大樂館的演出,當天就寫了履歷並寄了過去。我認為內心深處一定有什麼東西,但當時,這對我來說並不重要;這只是角色扮演。我只是想成為那樣!這就是我的意思。
藤原:就是這個!喜歡?
Oshiko :是的(笑)所以這是cosplay。毫無疑問。
藤原:哦,能給我一杯檸檬酸嗎?
俊子:那我就喝杯啤酒吧。哦,還有一碗咖哩100日圓。我也想吃那個!
我希望舞蹈變得簡單。
Oshiko :這與我之前提到的希臘和韓國戲劇有些聯繫,但我有一種潛在的品質,或者更確切地說,一種習慣,想要展示我不喜歡的東西。
有一個情節...
有一天,我坐在火車的優先座位。我是那種有空就優先坐的人,如果有人走到我前面需要,我就會讓出,但那天空了,我就坐在那裡看書平裝書不久,火車就變得擁擠起來,但我全神貫注於平裝書,沒有註意到。然後我聽到一個聲音說:「等一下。」當我向前看時,我的祖母就站在我面前。我旁邊有一位 40 多歲的女士,她說:“嘿,你有優先座位。”所以,我說,“哦,對不起”,當然我讓出了座位,但你認為我當時做了什麼? ?
藤原:呃…我不知道...咂舌嗎? ?
寧次:嗯,也許很接近了。我不是因為我想做,而是我自己做了,連我自己都感到驚訝……當時我表現得很不好。
藤原:啊…
Oshiko :我內心有這樣的渴望,我認為這在我的作品中表現得很明顯。不過,這就像是一種習慣。我說一些聽起來像是使命感的話,我在各國創作過作品,但當我意識到這就是我創作的根源時,我感到很沮喪。但我很沮喪,但還是放棄了(笑)
藤原:你覺得你就是這樣的人嗎?
俊子:是的。所以我想說的是,當我去看某人的作品時,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部分是創作者的那部分...這才是真正讓我感動的地方。我不知道如何解釋它,但最近我一直在提到“不可用的東西”之類的東西。正因為它是這樣一個“不能用的東西”,所以可以說它從來沒有被使用過。但「無法使用」並不是一個很好的詞,所以我必須想出一個更好的詞。
藤原: “不能用”,對吧?
寧次:是的。接下來,我想談談舞蹈,但首先讓我們回到密陽阿里郎節。 。在那之前,一切都與民族主義有關,但最終,每個人都開始圍繞著它跳舞。當我看到它時,年長的女性會跳上舞台,自己跳肩舞。
藤原:餵! ! !
Oshiko :我不認為當時的 Okkeechum 是關於民族主義的,它只是一種節奏,但我覺得舞蹈應該處理那些不被使用的東西。
藤原:啊。
根子:即使是民族主義也只不過是一段原聲片段。這不是一件小事,但我希望舞蹈能像那樣......
這時候,咖哩就派上用場了。

藤原:哦!太棒了!就像自製咖哩一樣。

未來發展
藤原:你想想看,很快你就要在紅磚倉庫進行新的演出了,對吧? 。
俊子:是的。這次我是主持人,所以我會考慮很多事情。我覺得有趣的是,當某件事出乎意料地發生時,例如一場事故,但在 300 個人中,只有 10 個人會覺得有趣。不過那10個人可能會震驚得哭著回家(笑)
藤原: 「好無聊」(笑)
根子:是的,沒錯(笑),但其他人似乎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但這不是我想做的事。

NEJI PIJIN / 都市民俗娛樂
<本次活動已結束。 〉
日期和時間: 6/25(週四)26(週五)27(週六)。
地點:橫濱紅磚倉庫1號館
*詳情請參閱相關活動。
Oshiko :另外,我現在感興趣的事情之一是思考舞蹈在觀看和被觀看的關係之外發生的條件是什麼,然後就是這樣。我認為戲劇是關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我認為這真的很棒。但舞蹈並不是關於這段關係本身。到目前為止,我一直在處理這些關係所產生的身體反應。如果我們繼續照原樣對待舞蹈,就會有一種感覺想要將自己從這種關係中抽離出來。我覺得跳舞的時候,你不必擔心有人在某個地方看著你。所以,舉一個容易理解的例子,我想做一些實際的事情,像是走進颱風眼,讓我的整個身體陷入其中,然後發明類似的東西。而且,我認為與幾個人分享比單獨做更好。例如大家都得了流感,發燒40度,就可以分享一下當時的身體狀況。
藤原:危險…但當你感冒時,你會奇怪地意識到自己的身體。
寧次:是的,確實感覺不是我。發高燒發抖的時候雖然很累,但也很有趣(笑)
藤原:無論你是否這樣做,這都是一個讓你更意識到自己日常行為的機會。
俊子:是的。因此,我正在尋找與我有同樣熱情並願意在此類事情上與我合作的人,並且我正在考慮在我們將他們聚集在一起後與他們進行為期三年的有限合作。
藤原:你要創立一家公司嗎?
俊子:是的。我認為將這些人聚集在一起並組建一家公司是個好主意。現在,我對這比創作新作品更感興趣。也就是說,你可能突然想創作一部新作品,那也沒關係。
藤原:當然。但為什麼限制為3年呢?
俊子:畢竟,要成為一個團體是很困難的。難道你不討厭自己逐漸疲憊而放棄嗎?
藤原:我真的很期待那家公司。
嗯,押子小姐是「滾石」(笑)
俊子:哈哈。我希望坡度盡可能少...
藤原:但是我認為「滾石」的一般比喻是,隨著它的滾動,角逐漸變得圓潤……但押子小姐可能不是這樣的(笑)。

完全的
這是店家資訊
這是我們這次點的菜

而今天的推薦是

肉和馬鈴薯的味道都很好!
立式酒吧下田店
神奈川縣橫濱市港北區綱島西1-6-4
電話:045-593-6437
營業時間: 16:00-24:00 (LO 23:30) *週日也營業
交通:從東急東橫線綱島站西口步行2分鐘



